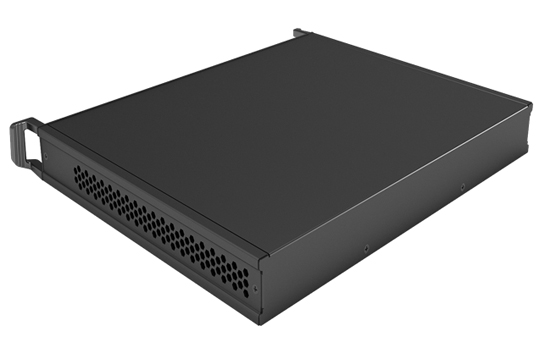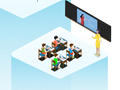一個國貧縣的教育逆襲——貴州省黔西南州望謨縣教育質量提升之路
http://www.prostar-power.com2020年11月06日 09:23教育裝備網
一張高考光榮榜,佇立在貴州省黔西南州望謨縣新屯村村口。榜上顯示:1962年,村里走出了第一個大學生;1993年,村里有了第一個留學生;今年,15名大學生榜上有名。
望謨是貴州省14個深度貧困縣中最貧困的縣之一,該縣副縣長、教育黨工委書記謝金金坦言,望謨窮在面上的是交通不發達,與外界的溝通聯系不順暢,但實質上而言,是窮在教育,貧在人才。
近年來,望謨縣把教育作為拔窮根的根本,把最好的資源給教育,教育質量實現快速躍升。今年,該縣本科錄取人數全州排名第三,書寫了窮縣辦好教育,學生“低進高出”的典范。
一切為教育讓路
從望謨縣城出發,沿縣道驅車大約兩小時,在樂元鎮平寨村平朗小學校門口,路“斷”了。
幾年前,平朗小學沒有圍墻,從望謨縣通往貞豐縣的縣道,就從學校教學區和生活區之間穿過。2017年,政府為了改善辦學條件,把這條縣道“斷”了,改由學校南面繞行,原來的縣道如今已是學校的跑道。
縣道變跑道,成為望謨“一切為教育讓路”的生動體現。
“望謨縣群眾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,是望謨縣貧困程度深、貧困面廣、脫貧任務重的主要因素之一。想要脫貧致富,不只先修路,更要重教育。”今年4月,在黔西南州教育大會暨全面實施教育立州戰略推進會現場,謝金金說。
近年來,望謨按照“高中聚集、初中進城、小學留鎮、村辦幼兒園、保留必要的教學點”的思路,進行校點布局優化調整,新建、改擴建了一批學校,學校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因布局調整而空出的編制,優先補充義務教育學校,全縣行政事業單位核定編制1萬多個,教育系統編制占到了一半以上。
在土地和經費緊張的情況下,望謨拿出最好的地塊建學校,優先安排教育資金。據望謨相關部門統計,2016年至2019年,平均每年縣級財政花在教育上的投入占全縣財政投入的23%。
望謨民族中學占地268畝,曾是縣里最平整的一塊土地。新校區建設初期,有人算過一筆賬,如果將這塊土地出售,差不多能賣4億元。這一數字與望謨縣2019年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當。
望謨民族中學副校長韋昌勇進入學校已32年,在他的記憶里,老校區只有4棟樓,校園只有新校區的五分之一大。
教師劉錦旭對那時“捉襟見肘”的情景記憶猶新:“學校面積太小了,學生很少做操,也沒有地方活動,一到冬天,一個接一個生病。搬到新校區,學生們的體質明顯好轉。”
最好的土地辦教育,最多的編制給學校,最多的經費在教育,望謨舉全縣之力,全面推動教育事業發展,徹底撕掉了教育弱縣的標簽。
學生“低進高出”
“來者不拒。”談起學校的生源,望謨縣實驗高中副校長劉秀祥說。
實驗高中今年680名學生參加高考,錄取318人。而3年前,這批學生的入學成績很低。
民族中學每年招生名額的一半是指標到校生,意味著每年都有文化課基礎較弱的學生入學。而自2014年高考錄取人數首次破百后,民族中學“一年一個樣”,今年,學校走出了905名大學生。
“低進高出”更能體現一所學校、一個地區的教育“硬實力”。
2015年8月,民族中學正式啟動申請貴州省級示范性高中。課堂優良率是一個重要指標,那一年,韋昌勇組建了一支由教務處、學科組長等組成的聽課小組,在全校開展聽課活動。
學校請來專家,給教師講什么是一堂好課,怎樣才能上好課。“老師眼里要有學生。”這是韋昌勇至今仍印象深刻的一句話。正是這樣的理念,改變了學校“滿堂灌”的課堂,從某種程度上也改變了學校。
為使理念落地,學校設計了“導入—學生自主合作探究—展示互動—教師總結—作業檢驗”的課堂教學模式,各科再結合實際形成本學科的教學模式。
2016年,民族中學成功創建三類省級示范性高中,結束了望謨沒有省級示范性高中的歷史。
最大的變化體現在課堂。“老師的提問有了回應。”韋昌勇說,學生參與課堂的積極性提高,思維能力得到提升,成績的提高水到渠成。
實驗高中近3000名學生中近一半是建檔立卡貧困戶子女,劉秀祥還記得剛入校時學生迷茫的眼神。他認為,最主要是先讓學生“找到自己”,激起內心的斗志。
對學生“低進高出”,劉秀祥深有感觸:“貧困地區的孩子,只要拉他一把,他就懂得感恩和努力。”
老師“陪”出來的進步
劉錦旭右胳膊內側有一條長長的疤痕。2018年5月,她在上班路上出了車禍,右胳膊肱骨骨頭粉碎性骨折。此時距離班上學生參加高考只有21天。
放心不下學生,出院第二天,劉錦旭打著繃帶回到班里看望學生,“別的班都有班主任送考,我也要去送我的學生”。高考完,她又全程指導學生填報志愿。當年,劉錦旭班上有45人考上大學,而她的右胳膊至今使不上勁。
當教師是個“苦”差事,用劉秀祥的話說:“學生的進步很大程度上是老師‘陪’出來的。”
劉秀祥一周有5天住在學校,他在學校的家就安在學生宿舍一樓。“不少學生從小就是留守兒童,他們缺失的關懷,很多時候需要老師填補。我們的老師,有的早上6點到校,晚上11點才回家。”
同事楊通鴻曾與劉秀祥一起查寢,規定早上6點起床,劉秀祥5點40分就等著播放音樂。晚上,教師和學生都睡了,他還在檢查。跟在劉秀祥身后,楊通鴻常常感動,他明白了“要給學生最長情的陪伴”,也明白了“做教育真的可以實現人生價值”。
民族中學食堂后面是教師公租房。“盡管學校沒有要求,但很多班主任都會主動申請住校,除了回家睡覺,其他時間都在教室和辦公室。”該校教師黃秋梅說,有的教師盯完早讀,再送孩子上學。
韋昌勇提及對教師激勵政策,縣里出資給全校教師發獎金,每人每年最多的能拿到近3萬元,職稱評定、崗位晉升和評獎評優也會有優待。
劉秀祥回到家鄉的8年,是望謨教育快速發展的8年,也是望謨百姓扭轉“讀書無用”觀念的一個階段。從很多人上不起學到沒有一人因家庭貧困輟學,從考不上大學到能考上大學、改變命運,鄉親們看到了讀書的力量,反過來更重視教育,更加認識到教育是徹底改變世代貧困宿命的根本,是真正能走出大山的那條路。
責任編輯:董曉娟
本文鏈接:TOP↑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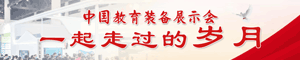






 首頁
首頁